
在中国古代政区演进的长卷中,清代创设的“厅”制是一种独特的存在:不同于传统的府、州、县,是一种专为应对治理复杂情况而生的弹性政区,主要存在于民族杂处、地形交错、治理难度较大的地区,如东北、川边、云贵、新疆、甘肃、台湾以及内地个别区域。这些地方设府立县的时机尚不成熟,又亟须强化管控,清政府便设“厅”治之。这些“厅”或直隶于省,或隶属于府,成为将国家秩序精准嵌入特殊地区的“制度楔子”。
本期专栏聚焦清代推行“厅”制的两个典型地域——川边与东北。在藏彝走廊,它以灵活的设置,将国家治理的触角深入高山峡谷,催生了多民族交融的家国记忆;在关外“龙兴之地”,它则从化解旗民纠纷的理事机构,逐步演变为安民抚众、镇守边疆的抚民政区。“厅”这一独特政区制度承载着务实的治理智慧,诠释着“因俗而治”“多元一体”的生动实践。
展开剩余90%东北“厅”制
跨越百年的边疆治理探索
曲华文
在清代地方行政制度的体系中,东北地区的“厅”是个特殊存在——它既不是沿用千年的州县,也不是八旗专属的驻防体系,而是清廷为破解边疆治理难题,量身打造的“混搭型”行政单元。从乾隆年间萌芽的理事厅,到光绪朝遍地开花的抚民厅,再到清末边疆要地的直隶厅,“厅”制在东北走过百年历程,不仅见证了旗民杂居的社会变迁,更藏着清代边疆治理从“身份管理”到“地域治理”的深层逻辑。
旗民杂处催生出的“中间方案”
清代入主中原后,东北地区作为“龙兴之地”,实行了独特的“旗民分治”制度:旗人归盛京、吉林、黑龙江三将军麾下的八旗系统管辖,民人(多为关内移民)则由奉天府下辖的州县管理。可现实却给这套制度出了难题——顺治、康熙两朝先后五次颁布“移民招垦令”后,大量民人涌入东北,柳条边内的旗地与民地犬牙交错,原本清晰的旗民划界变得模糊。
民人住旗地、种旗田,旗民之间的土地纠纷、司法诉讼经常发生。按旧制,旗官管不了民人,民官管不了旗人,一桩案子往往要来回推诿。例如乾隆二十七年(1762年),凤凰城赛马集民人郭纬抗法殴官,办案时竟发现,这里的民人赋税归几百里外的辽阳州收,司法案件则可能分属海城、承德等多个州县管辖,最后甚至连该追责哪个官员都查不清。
这种“管理真空”,使得“厅”应运而生。乾隆初期,清廷在民人稀少却纠纷频发的旗地设“理事厅”,主官带“理事衔”——既能管民人的赋税、官司,又能处理旗民之间的纠纷,相当于在旗、民两套管理体系间架起了“桥梁”。例如乾隆十二年(1747年)设立的吉林理事同知,就把原本归奉天府管的民人事务,划归吉林将军管辖,成了东北“厅”制的起点。
从“理事”到“抚民”的功能升级
早期的理事厅更像“应急机构”,甚至没有固定辖区,例如吉林厅在初设时,管辖范围和吉林将军辖区相近,只能按“身份”管民人,没法按“地域”划边界。但随着东北封禁渐开,移民越来越多,理事厅慢慢“长大”,变成了真正的行政单元。
嘉庆朝是东北“厅”制发展的关键节点:嘉庆五年(1800年),长春厅设立;嘉庆十二年(1807年),昌图厅设立;嘉庆十八年(1813年),新民厅设立,“厅”的数量开始稳定增长。这些厅不只是聚焦“旗民纠纷”,更要管百姓的日常生计——岫岩厅设了37个“社”作为基层组织,配备198名乡约、396名保正,从收税到户籍,再到婚丧诉讼,样样都管;呼兰厅更是从“只管司法”升级到“统管地方”,同治三年(1864年)明确辖区边界,把旗民管理从“按身份分”改成“按地域分”,成了黑龙江设郡县的开端。
到了光绪朝,“厅”制又迎来一次大变身——从“理事厅”改成“抚民厅”。这并非简单地换名字:以前理事厅官缺多是满缺,改成抚民厅后,满汉官员都能任职;以前侧重“平纠纷”,现在更强调“安百姓”。例如光绪七年(1881年),长春厅、伯都讷厅都从理事厅改成抚民厅,官员开始主动招抚移民、兴修水利,甚至推动农业技术改良。据道光《吉林外记》记载,抚民厅的衙署布局和吏役设置都按照州县规制,设有六房吏员、马快、民壮等,相当于一个“微缩县政府”。
守护边疆的最后一道防线
清末的东北,边疆危机日益严重,“厅”又承担起了新使命——变成“直隶厅”,镇守边疆要地。和普通抚民厅不同,直隶厅直接隶属于将军或道管辖,不用绕到府一级,响应更快、权力更集中。
光绪二年(1876年)设立的凤凰直隶厅,是东北地区第一个直隶厅,地处中朝边境,主官带“兵备衔”,既要管民政,还要守边防,相当于“军政合一”的据点。后来黑龙江设的瑷珲直隶厅、呼伦直隶厅,吉林设的珲春直隶厅,也都建在中俄、中朝边境,成了抵御外侵、稳定边疆的“桥头堡”。这些直隶厅不再和旗官同城办公,有独立的辖区和行政中心,例如营口直隶厅地处沿海,专门管通商和海防,短短几年就成了东北的商贸重镇。
到光绪三十三年(1907年)东北改设行省前,全东北已设有近20个抚民厅、11个直隶厅。从最初的“补丁式”机构,到后来的“民生管家”,再到最后的“边疆卫士”,“厅”的角色变迁,正是清代东北治理的生动缩影——清廷不再执着于“旗民分治”的旧规矩,而是根据实际治理需求调整制度,用更灵活的方式管理这片广袤的土地。
“厅”制背后的治理智慧
回望清代东北地区的“厅”制,它或许并非完美的行政制度——有的厅职能不全,有的辖区混乱,甚至清代政书对“厅”的定义也存在分歧。但恰恰这种“不完美”,开云官方app下载彰显了清代治理者的务实精神。他们没有生硬套用内地的州县旧制,也没有固守东北的民族传统,而是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,以“厅”这种新型行政单元,有效化解了边疆治理的困境。
从旗民杂居的治理混乱,到行省制度的最终建立,“厅”就像一块“过渡石”,见证了东北从“龙兴之地”到“边疆要区”的战略定位转变。它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:好的治理制度,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“模板”,而是能跟着时代走、贴着百姓需求变的“活方案”——这或许就是清代东北“厅”制,留给今天最有益的历史启示。
川边“厅”事
藏彝走廊的行政区划智慧
{jz:field.toptypename/}董嘉瑜
提到“厅”,今天我们多会想到办事机构或建筑空间,却少有人知,在清代的行政版图上,它曾是守护边疆、融合民族的独特政区形态。在川西高原与横断山脉交织的“藏彝走廊”间,清代川边地区(含川西、川西北高原及川西南山地)设立的10个“厅”——3个直隶厅、7个散厅,不仅是王朝治理边地的创新实践,更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长的鲜活注脚。
从“办事点”到“行政区”
——清代“厅”制的由来
清代地方行政本以“省—府—县”三级为骨架,“厅”的出现,是加强属地治理的制度创新。最初,知府常会派同知、通判等辅助官员到府内偏远或特殊区域驻守办事,这些官员的办事点便被称为“厅”。若只是处理专项事务,“厅”仍属官员办公场所;可当这些驻点官员逐渐掌握了辖区内“刑名钱谷”(司法、赋税)等完整管理权,并拥有固定管辖范围时,“厅”便从“事务机构”变为正式的“政区厅”,即我们所说的行政区划。
从层级上看,“厅”分两类:地处战略要冲、治理难度大的“直隶厅”,直接隶属于省级政府;规模较小、事务较简的“散厅”,则隶属于府级行政区。这种弹性设置,让“厅”成为清代应对复杂地域治理的“灵活工具”,而川边地区,正是这一工具的重要实践场。
为何是“厅”
——川边治理的现实选择
明代川边长期实行“土司+卫所”的复合管理模式:土司统辖当地部族,卫所负责军事戍守,朝廷对地方的直接管控有限。清代,随着“卫所裁改”(取消军事卫所,归入地方行政)与“改土归流”(废除土司世袭,派流官治理)的推进,川边需要新的政区形态承接治理职能——为何最终选择“厅”,而非更常见的“府”或“州”?
答案藏在清代“定额治国”的理念里。清代财政收入相对稳定,官员编制严格控制,不愿为新设政区大幅增加行政成本。而“厅”的优势恰好在此:它依托府级已有的辅助官员(同知、通判)设立,行政成本与财政投入处于可控状态。同时,“厅”的建制灵活,办事机构可深入偏远区域,能很好适配川边复杂地形和多民族杂居的治理需求。雍正七年(1729年),打箭炉厅(今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市)设立,成为清代川边“厅”制的起点,也开启了边地治理的新篇章。
半月形”到“全域覆盖”
——川边“厅”的百年布局
川边“厅”的设置并非一蹴而就,而是伴随王朝对边地认知的深化逐步推进,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:
前中期:环盆地的“半月屏障”
乾隆年间,清廷加大对川边的开发力度,在打箭炉厅之外,陆续设立杂谷厅(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)、松潘厅(今阿坝州松潘县)、懋功厅(今阿坝州小金县)3个厅,并相继升为直隶厅。另外,也设有雷波厅(属叙州府)、越巂厅(属宁远府)、马边厅(属叙州府)3个散厅。到嘉庆十四年(1809年)峨边厅(属嘉定府)设立时,这些“厅”已形成环绕四川盆地西、北、南缘的“半月形”分布,像一道屏障,将内地治理模式逐步向高原延伸。
清末:应对边疆危机的“深度拓展”
19世纪末,西南边疆危机加剧,清政府平定土司叛乱后,在川边推行大规模改土归流,“厅”制迎来新一轮扩张。一方面,打箭炉厅因地处川藏交通要冲,战略地位日益凸显,光绪二十九年(1903年)由散厅升为直隶厅,宣统三年(1911年)再升格为康定府,成为经略康藏的核心;另一方面,里化厅(今甘孜州理塘县)、三坝厅(今分属理塘县、巴塘县)、盐边厅(属宁远府)3个散厅相继设立,将“厅”的覆盖范围推向川边腹地。
至清末,川边地区共有3个直隶厅、7个散厅,占当时四川省直隶厅总数的75%、散厅总数的70%。这组数据背后,体现出“厅”作为川边核心政区的重要地位,更彰显了清廷将国家治理触角深入藏彝走廊的坚定决心。
治所里的治理逻辑
——从“土司驻地”到“行政节点”
治所(政府驻地)是行政区划的“灵魂”,川边“厅”的治所选择,藏着边地治理的独特逻辑。因川边多高山峡谷,且易受山洪、地震影响,“厅”的治所很少是内地那种规整的“四方城池”,而是多从三类地点改造而来:
有的源于土司驻地,如打箭炉厅、懋功直隶厅,依托原有部族统治中心,减少治理阻力;有的来自卫所驻地,如松潘直隶厅、越巂厅,借助旧有军事机构的防御基础;还有的由军事堡垒或巡检司驻地改建,如马边厅、峨边厅,契合边地安防需求。
这些治所虽形态不规则,却都是清廷向川边施加政治影响的“节点”:朝廷不仅投入财力修缮城池、加固城门,更以治所为中心,推行赋税、司法、教育等制度,让“国家认同”沿着山间驿道,渗透到每一个村寨。以打箭炉厅为例,其治所康定既是川藏贸易的“旱码头”,又是稽查往来人口、促进汉藏交流的“桥梁”,真正实现了“以孤城而控制诸地,以一隅而屏藩全藏”。
“厅”的落幕与遗产
——藏彝走廊上的家国记忆
1913年,北洋政府颁布《划一现行各县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》,将清代所有“厅”统一改为“县”,这个存续200余年的独特政区形态,正式退出历史舞台。但川边“厅”制留下的遗产,却深刻影响着这片土地。它结束了川边长期“间接治理”的历史,让朝廷的政令第一次真正畅通于藏彝走廊;它以灵活的建制,平衡了行政成本与治理需求,成为边疆政区设置的经典案例。更重要的是,“厅”的设立与运作,促进了汉、藏、彝等多民族在经济、文化、生活上的深度交融,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长埋下了种子。
发布于:北京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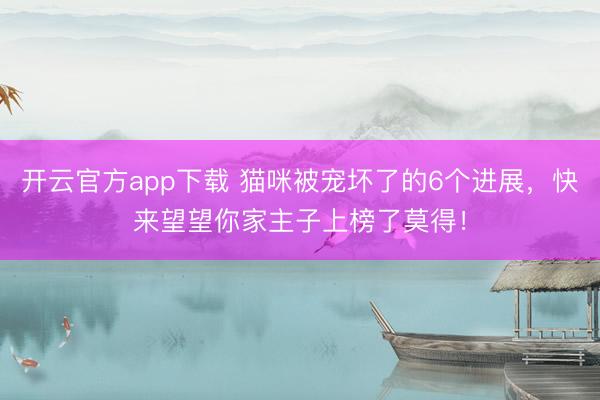


 备案号:
备案号: